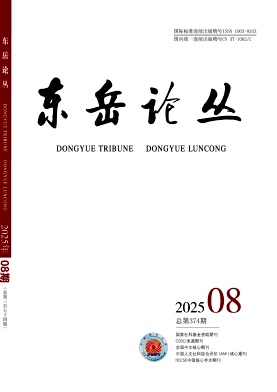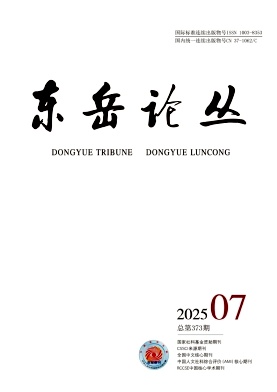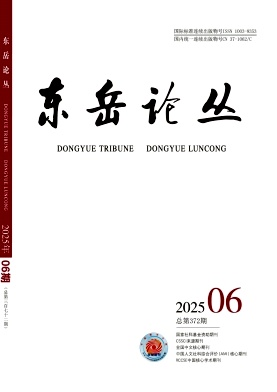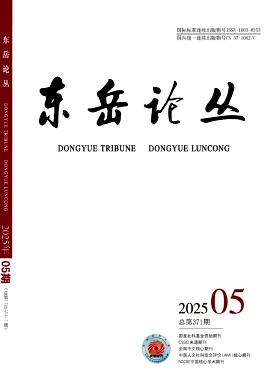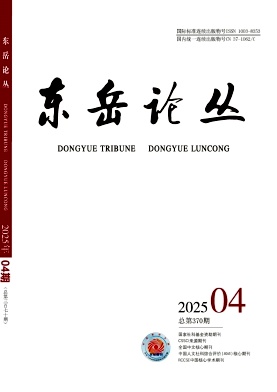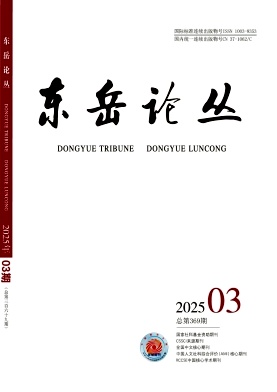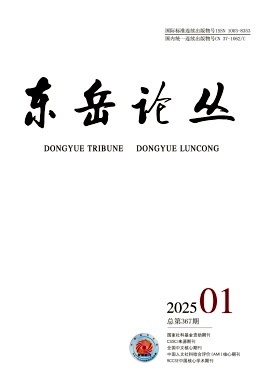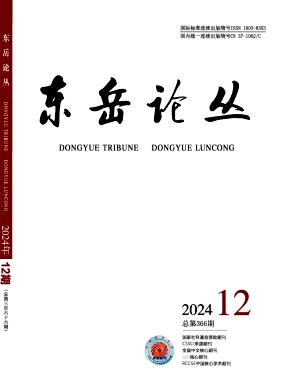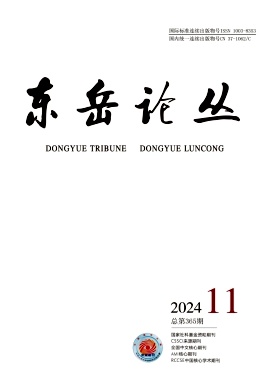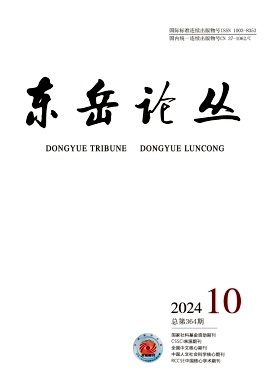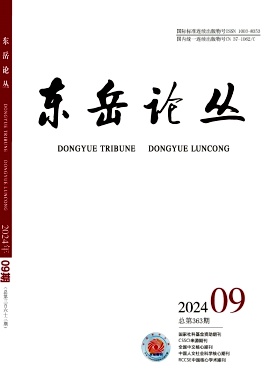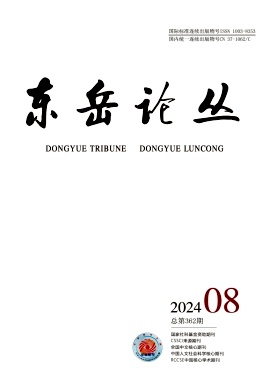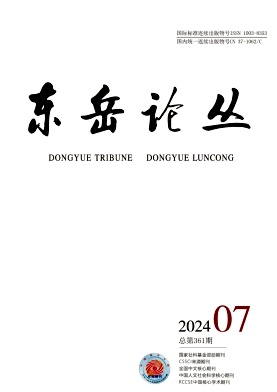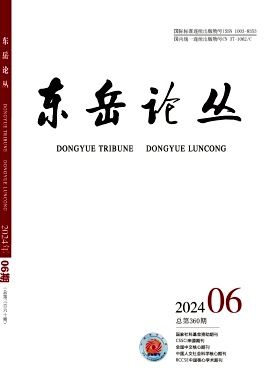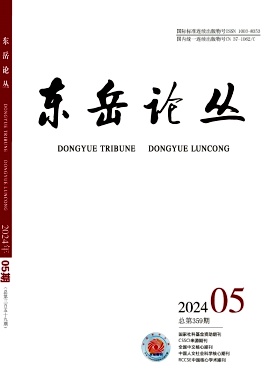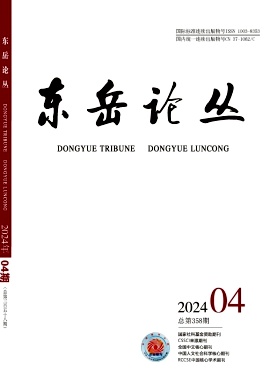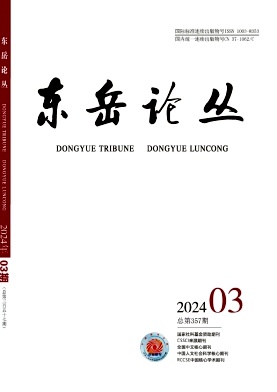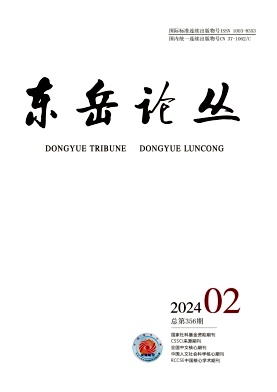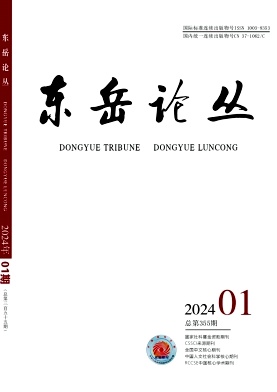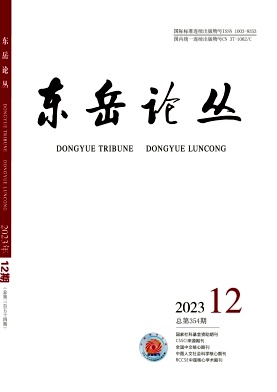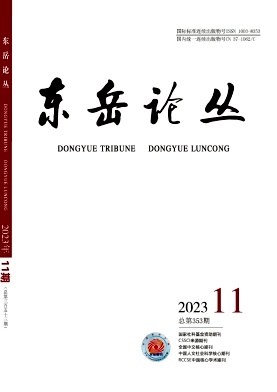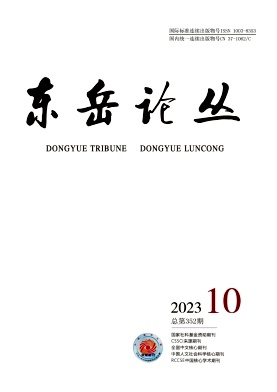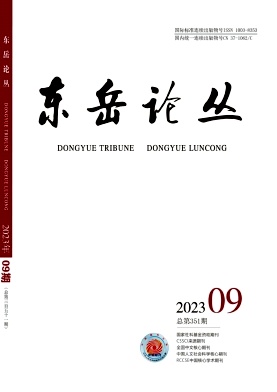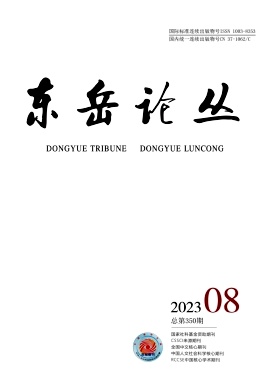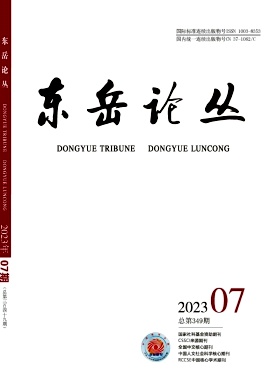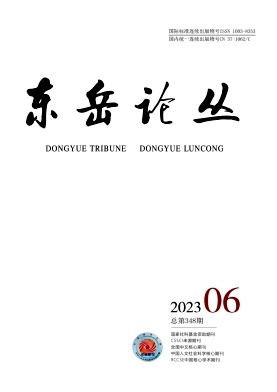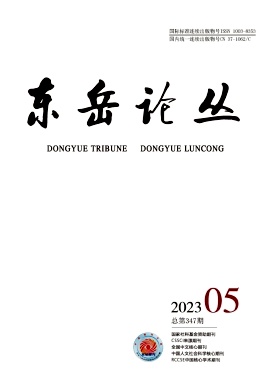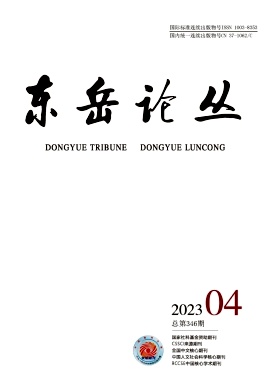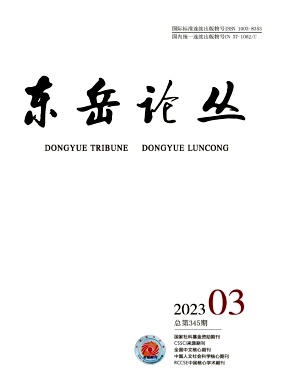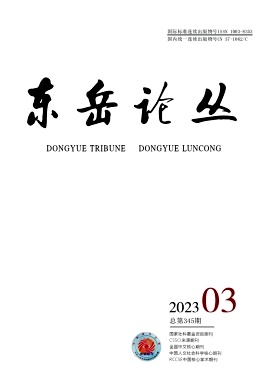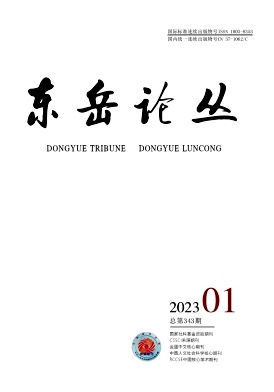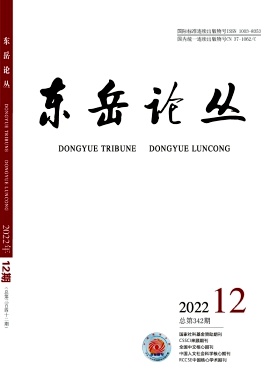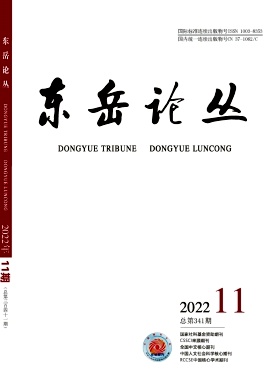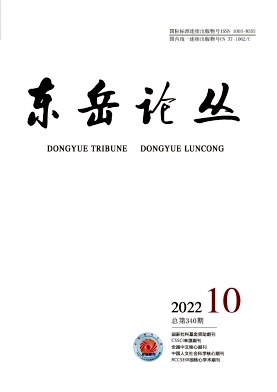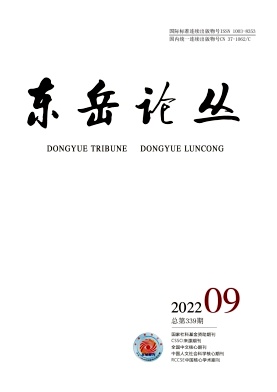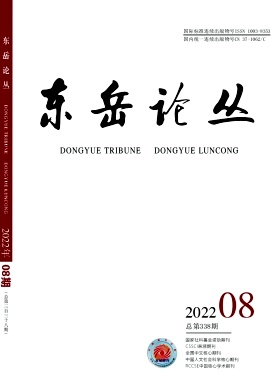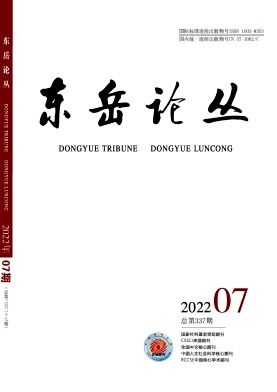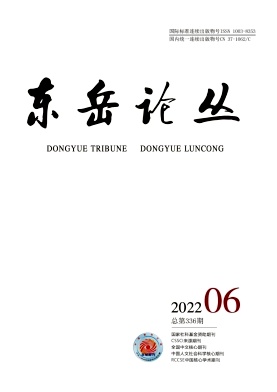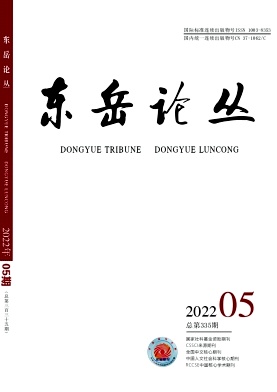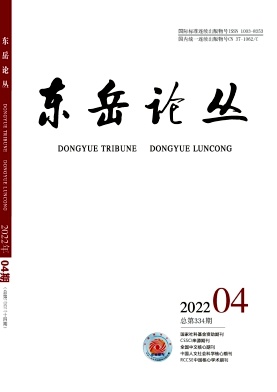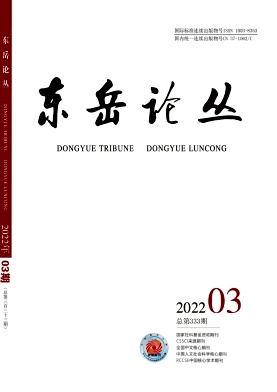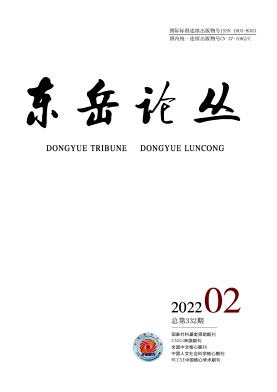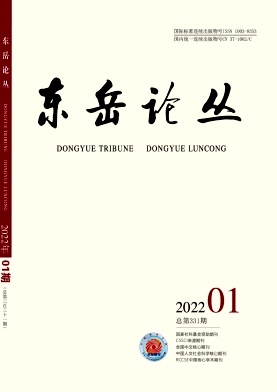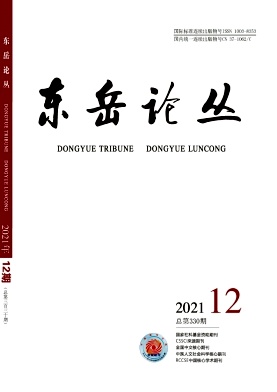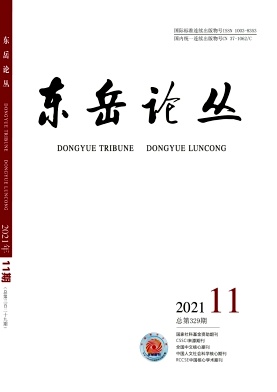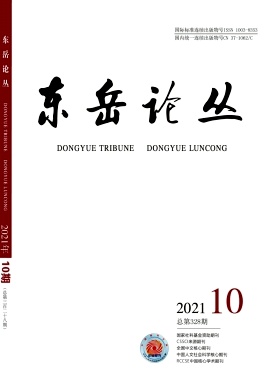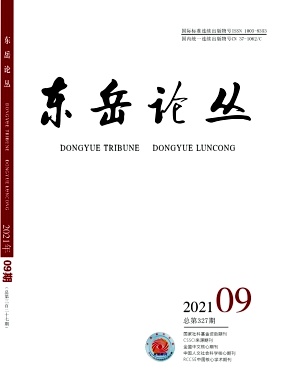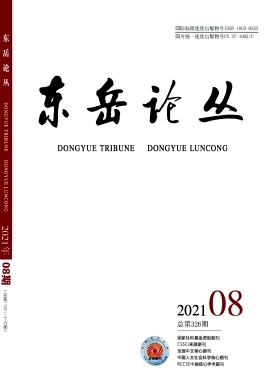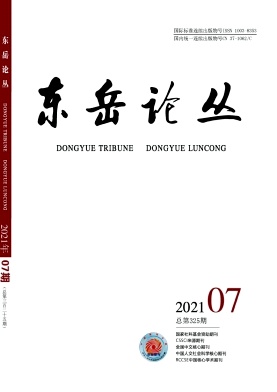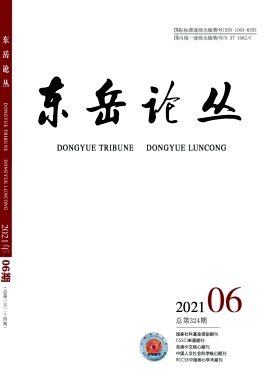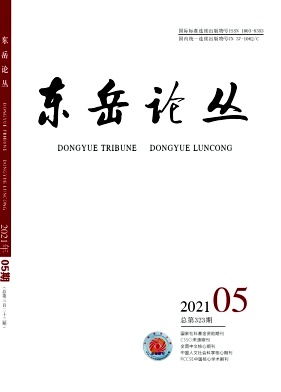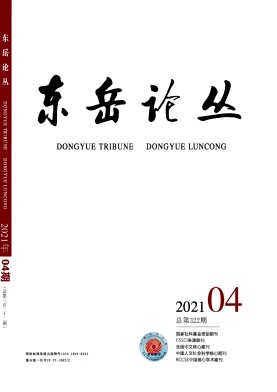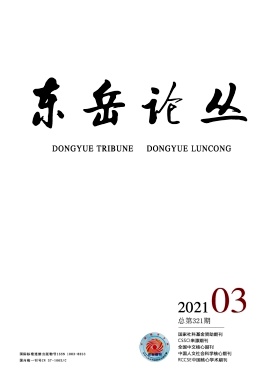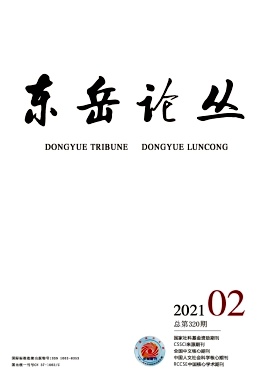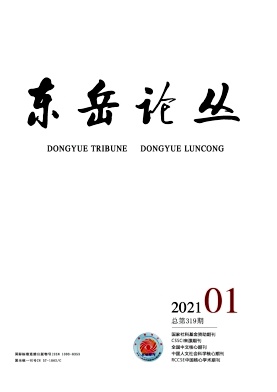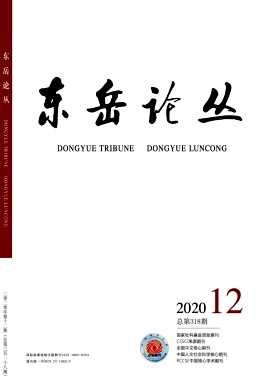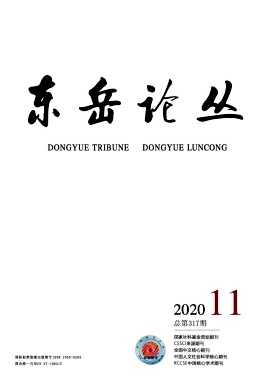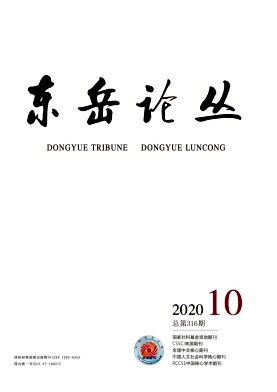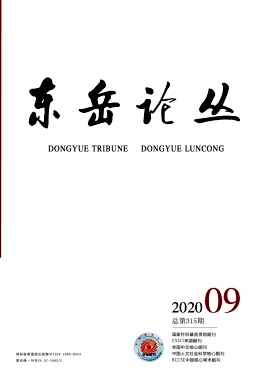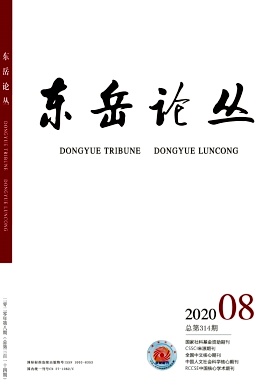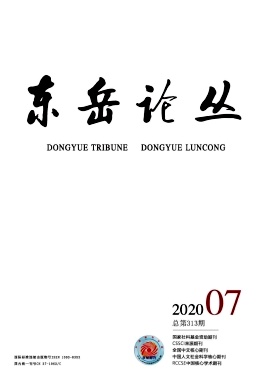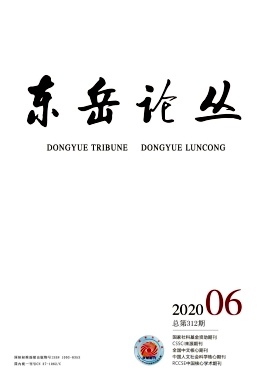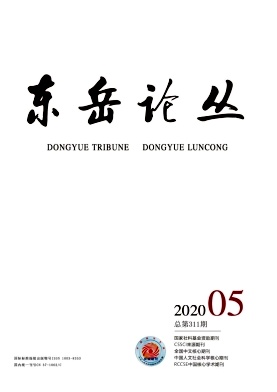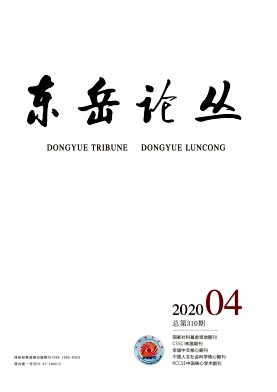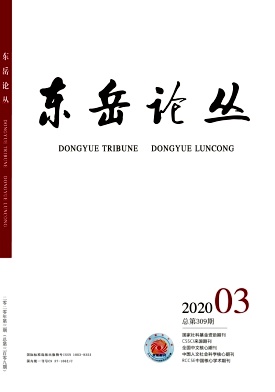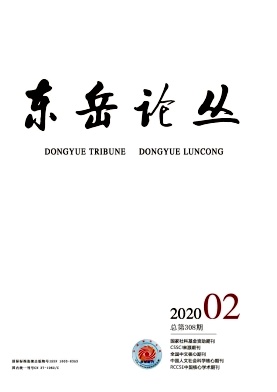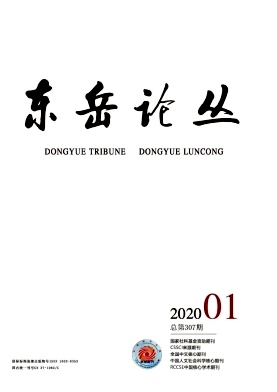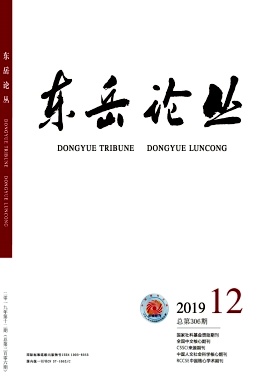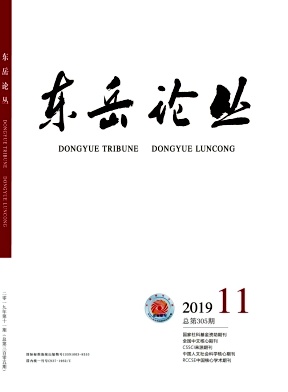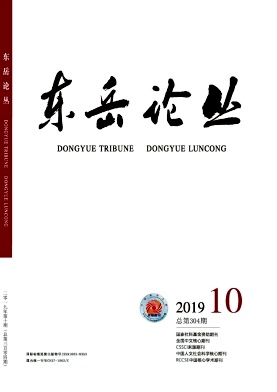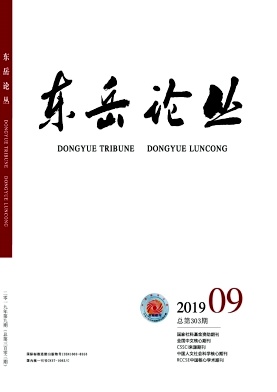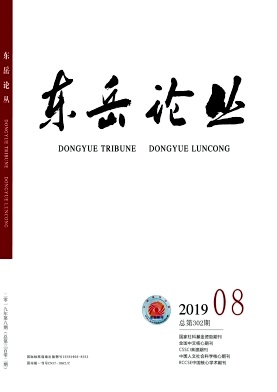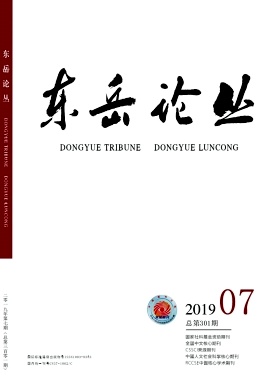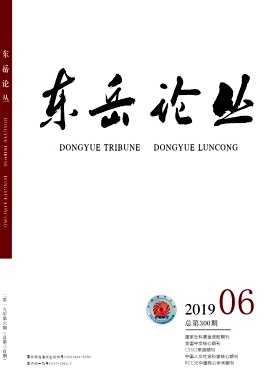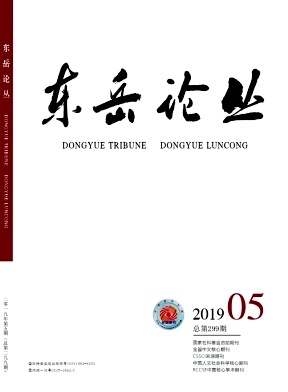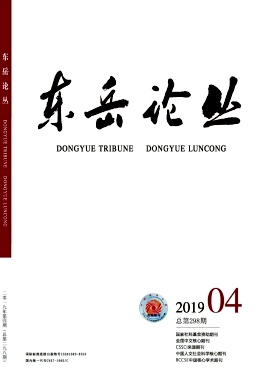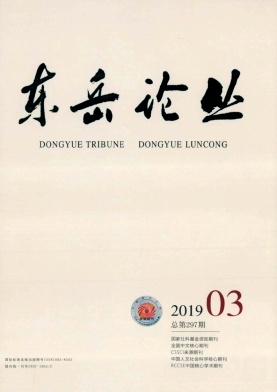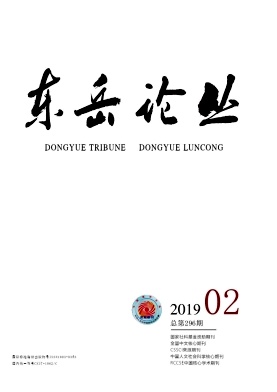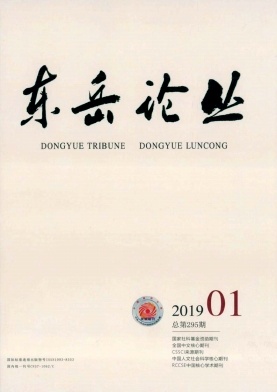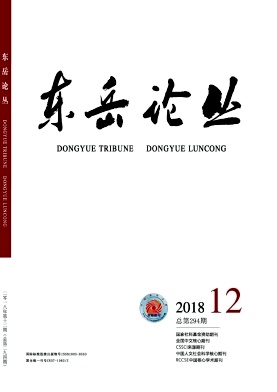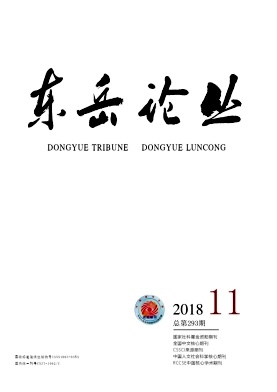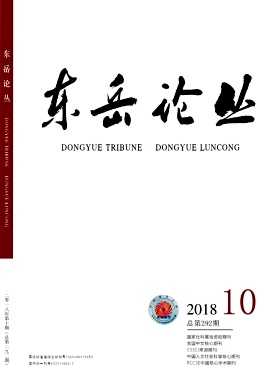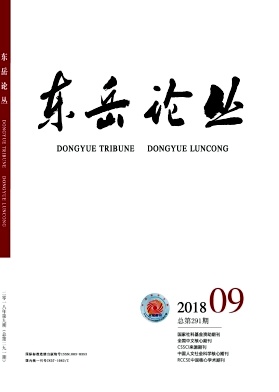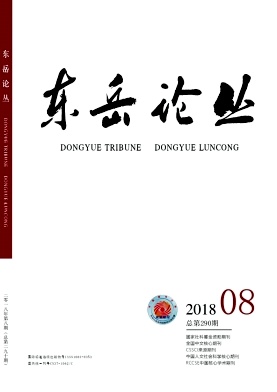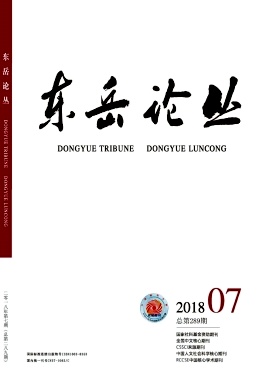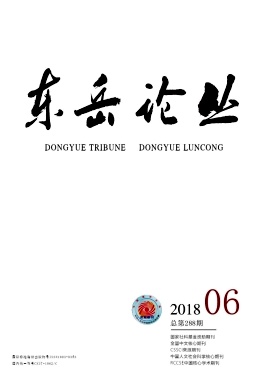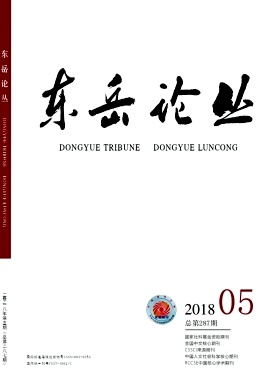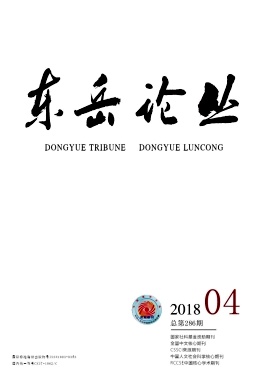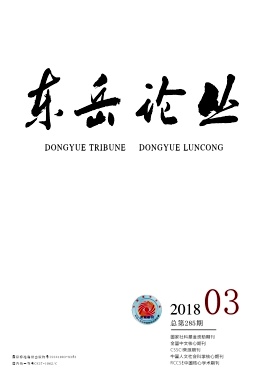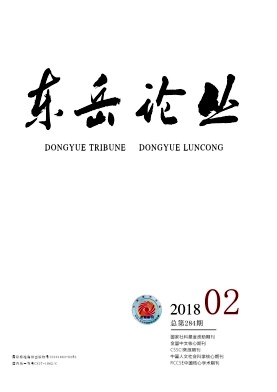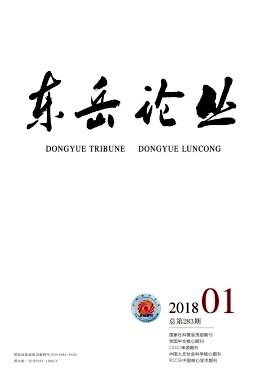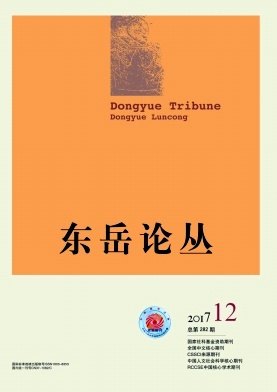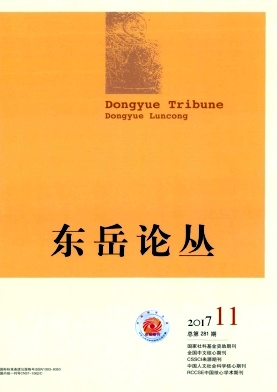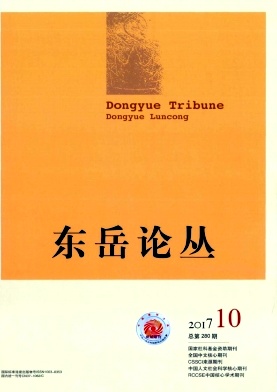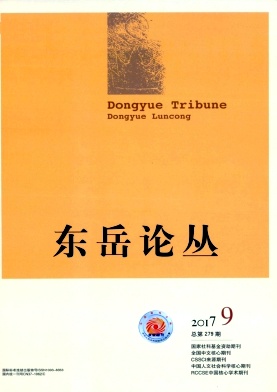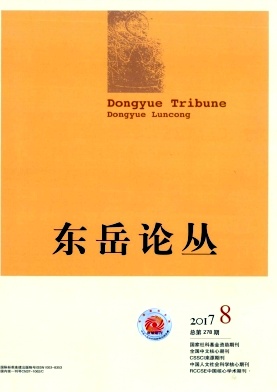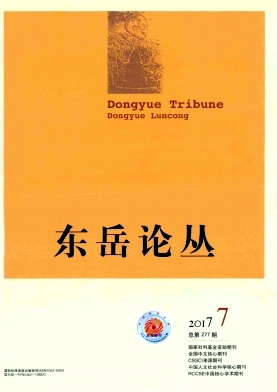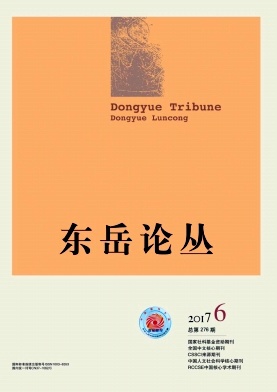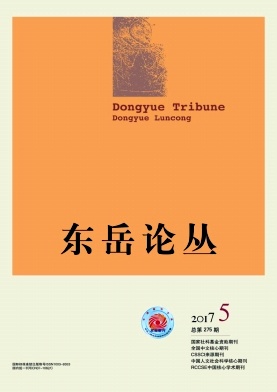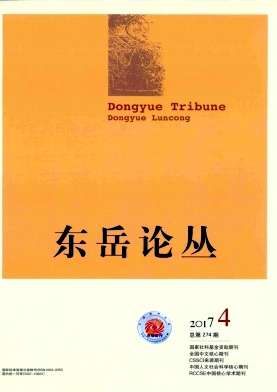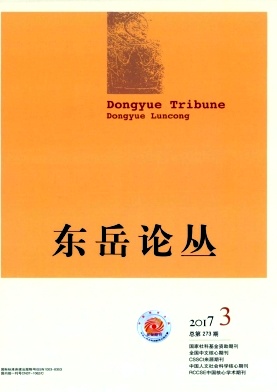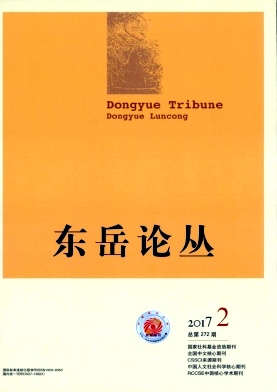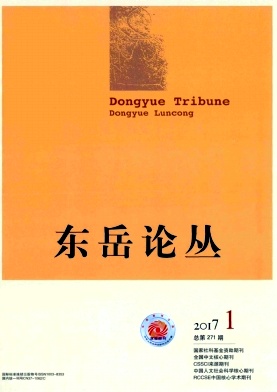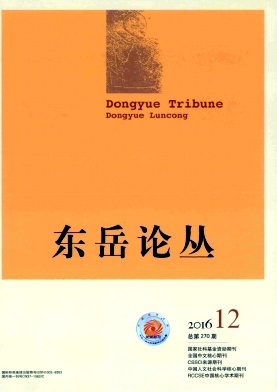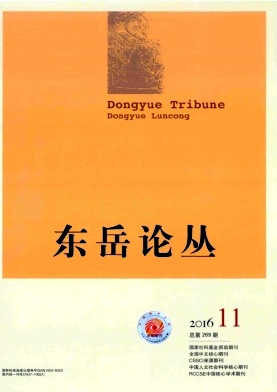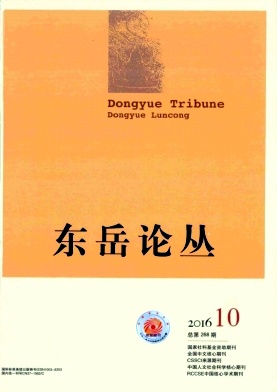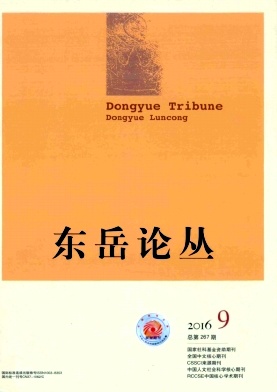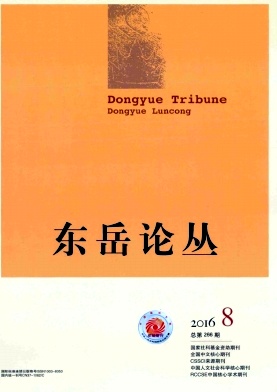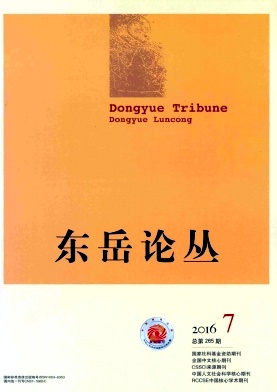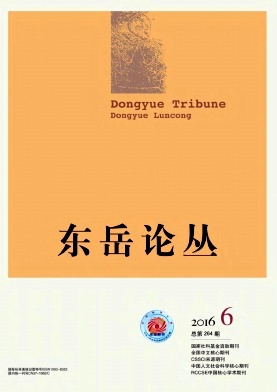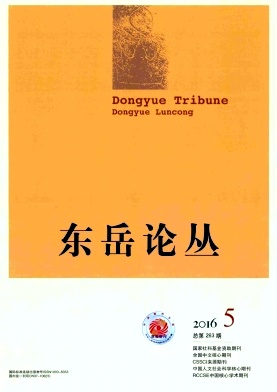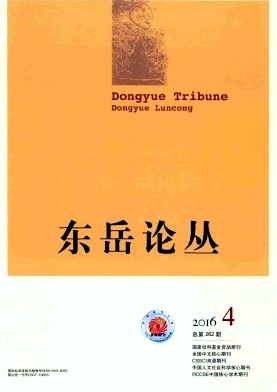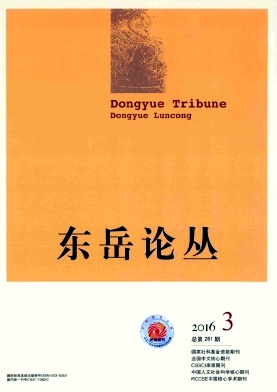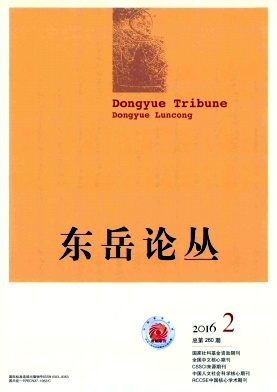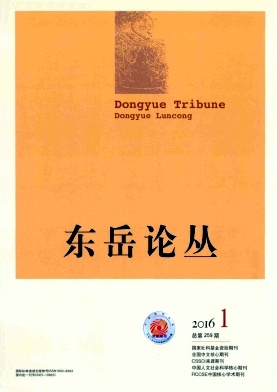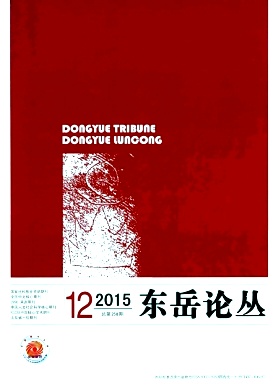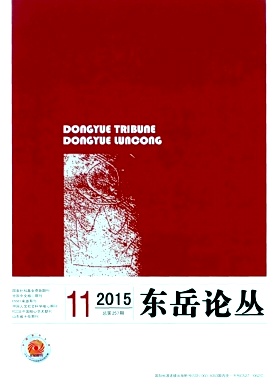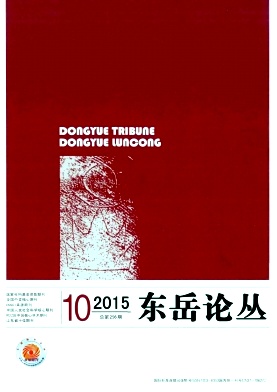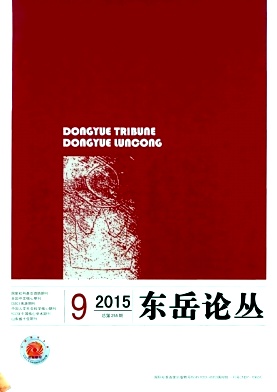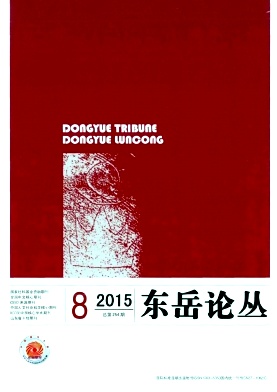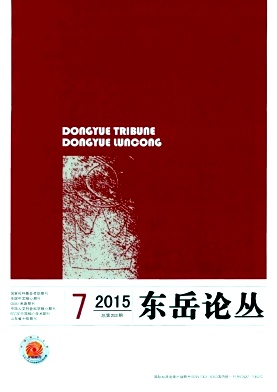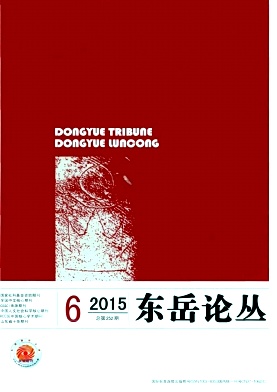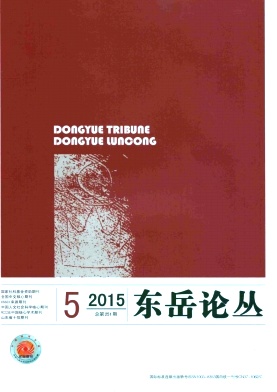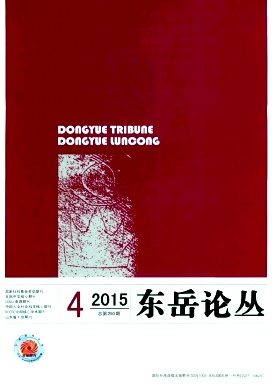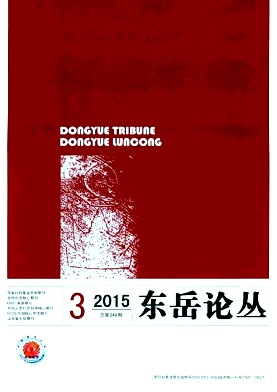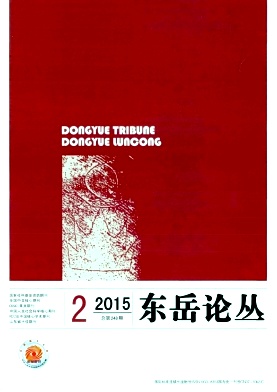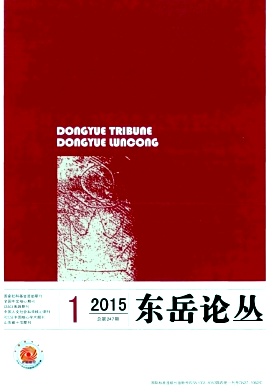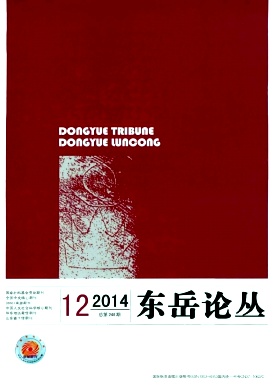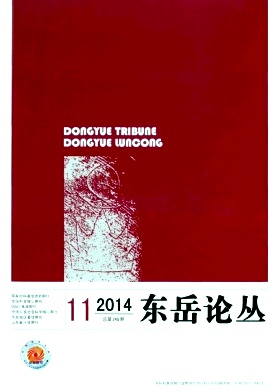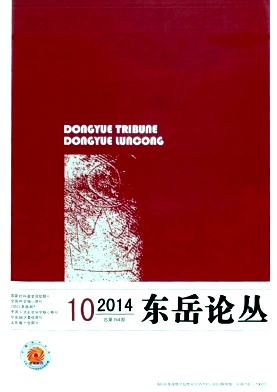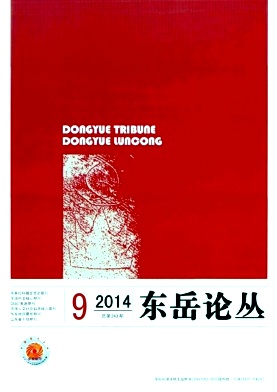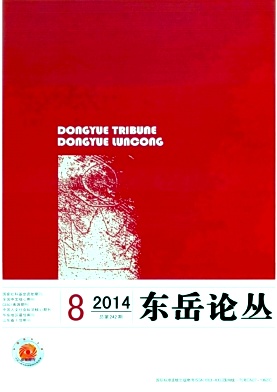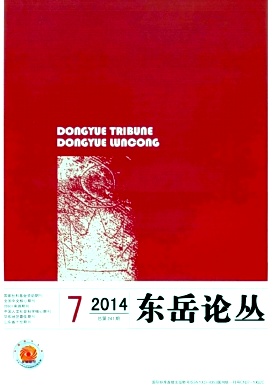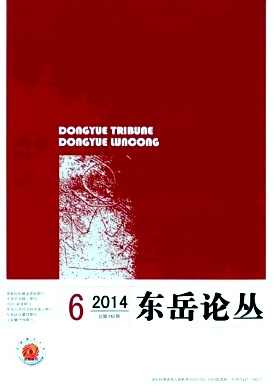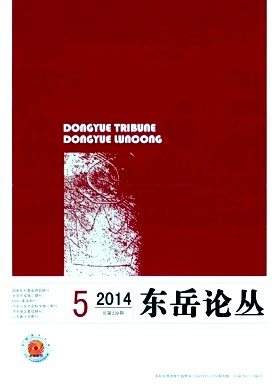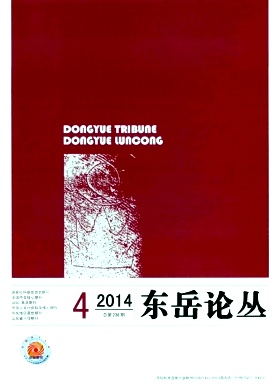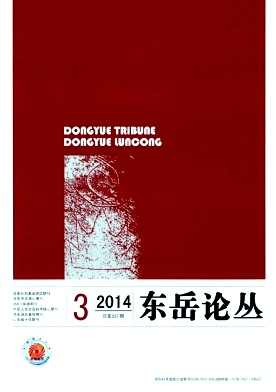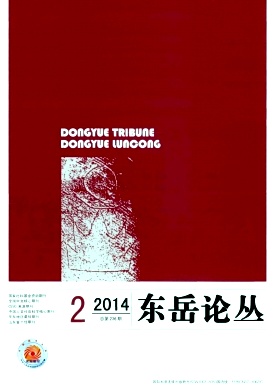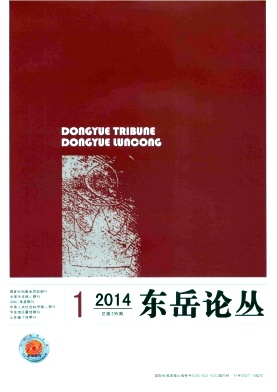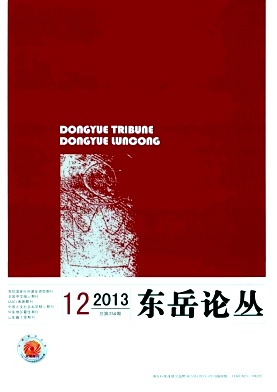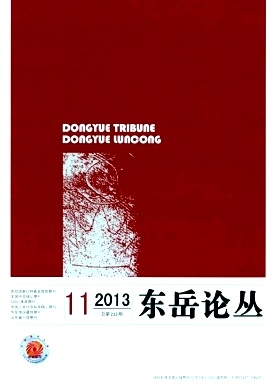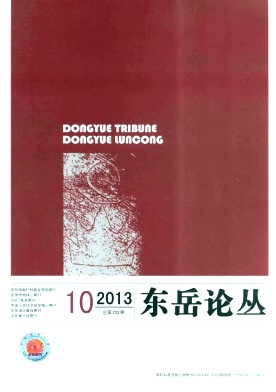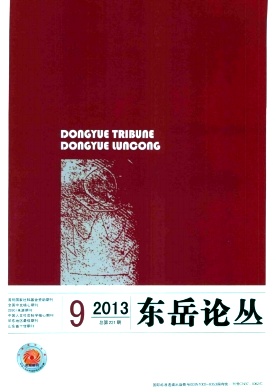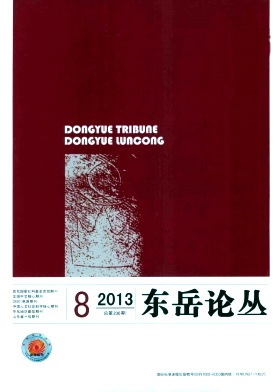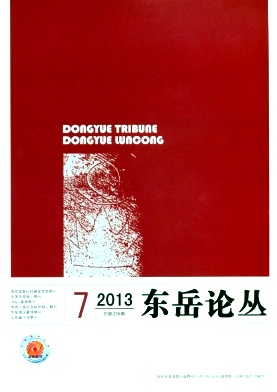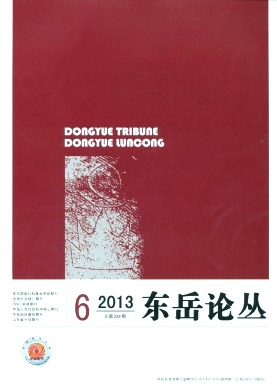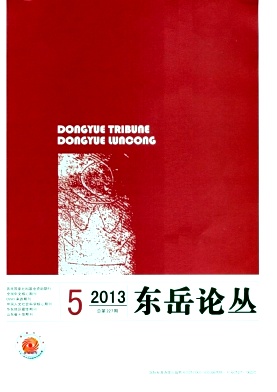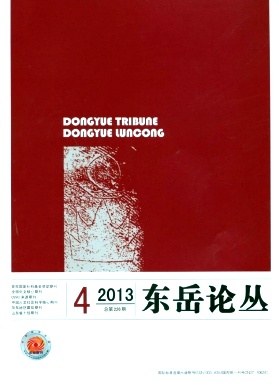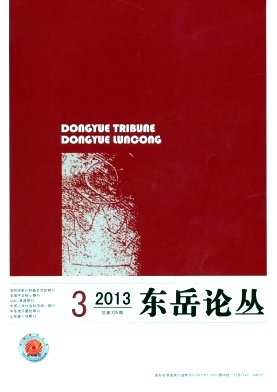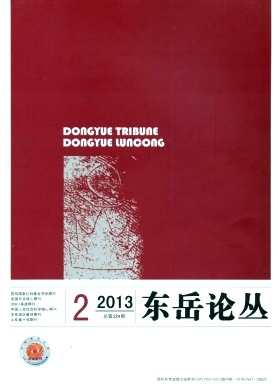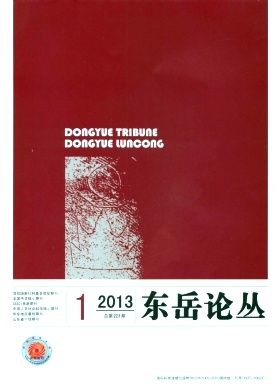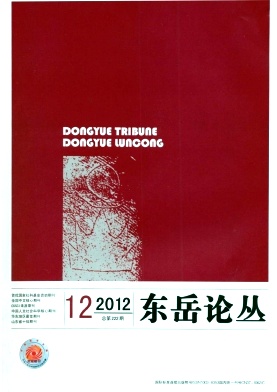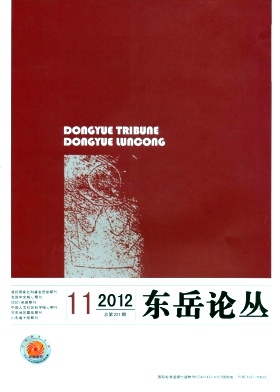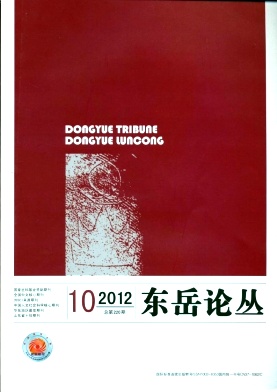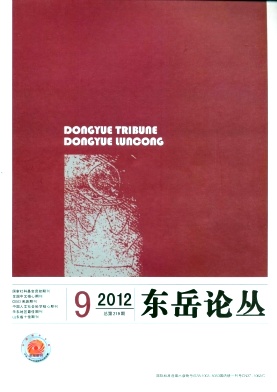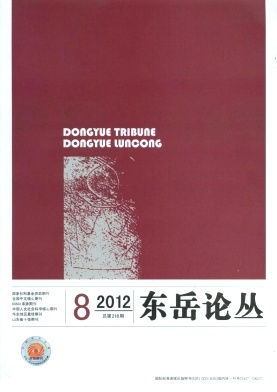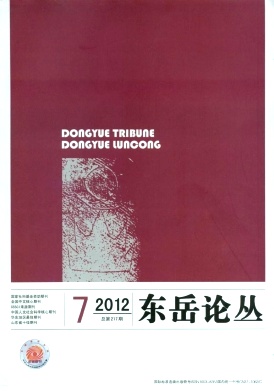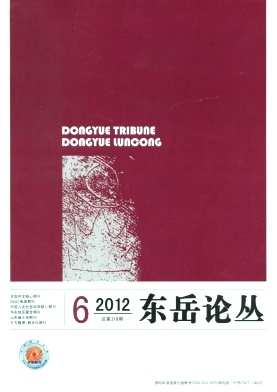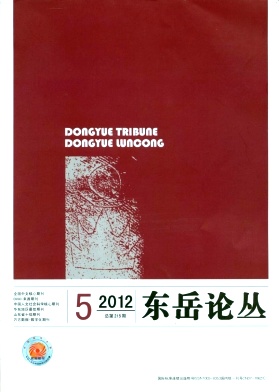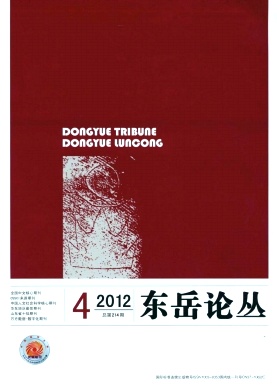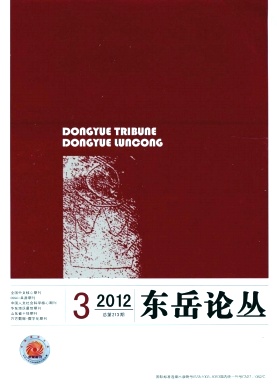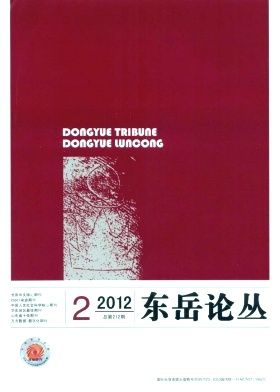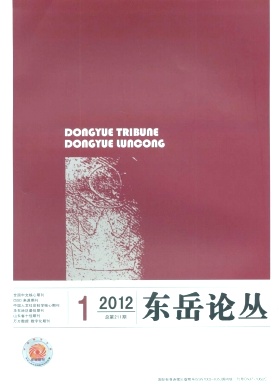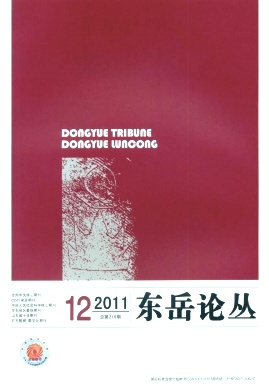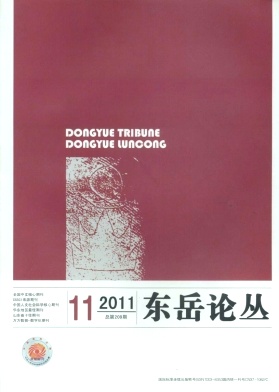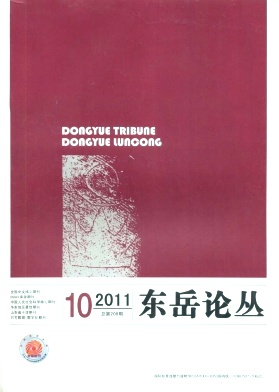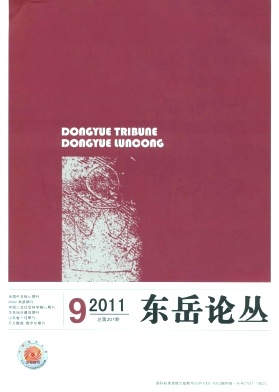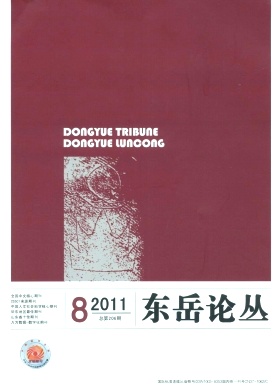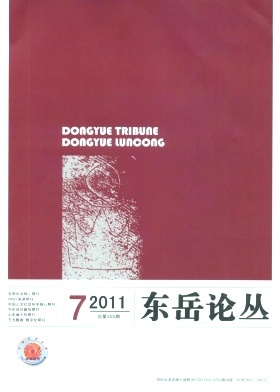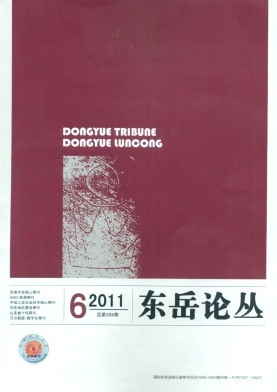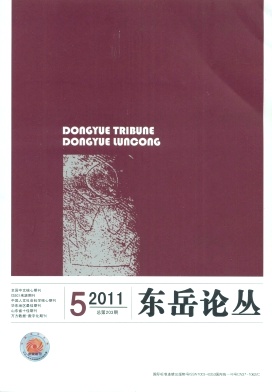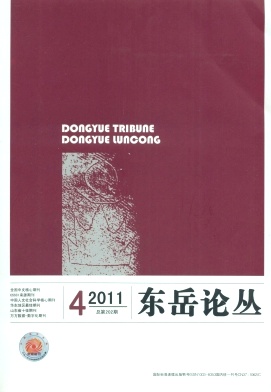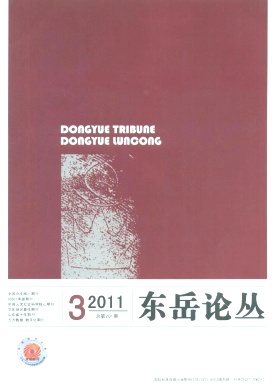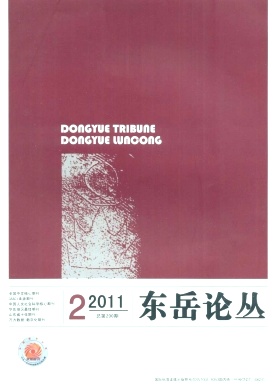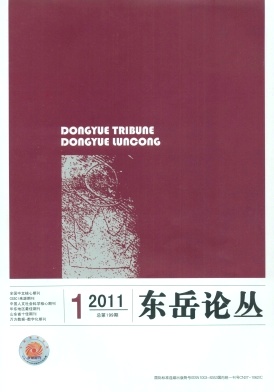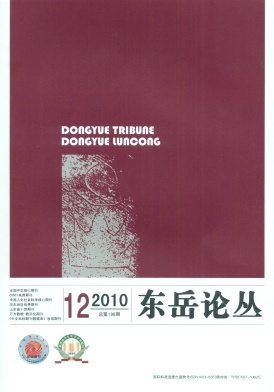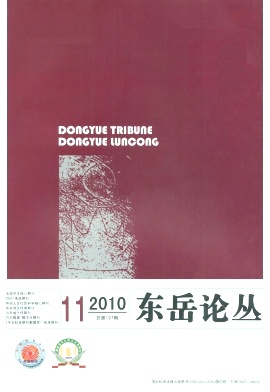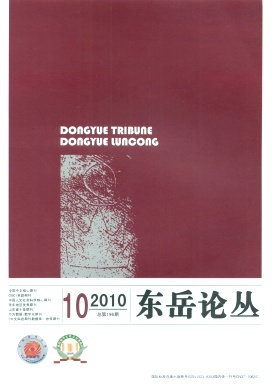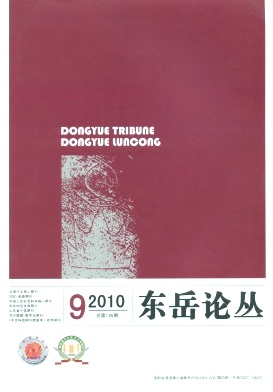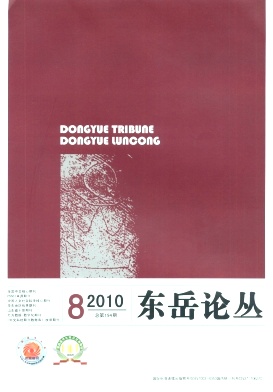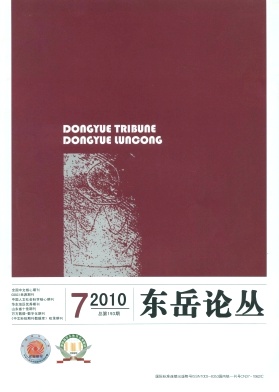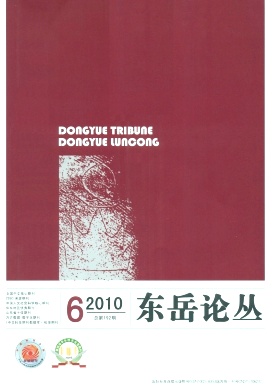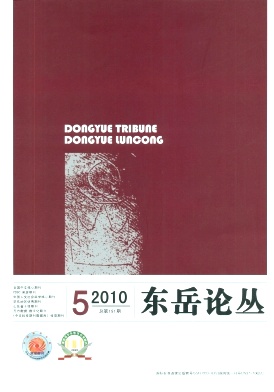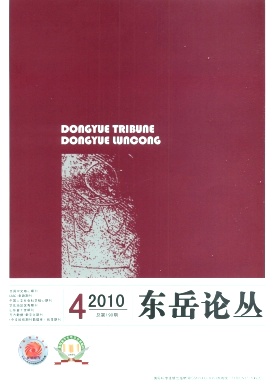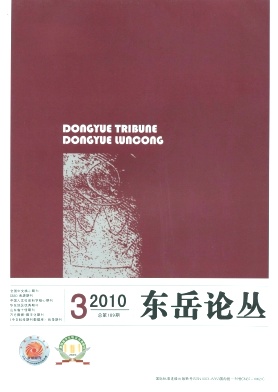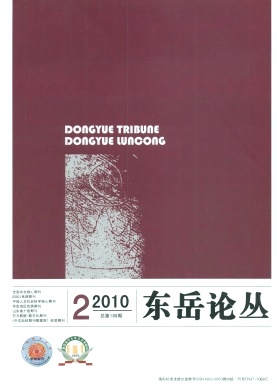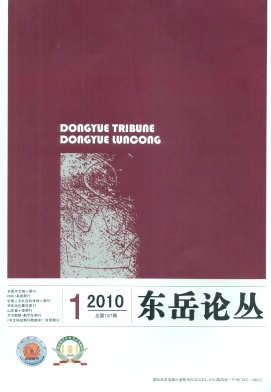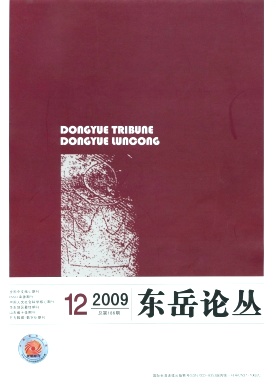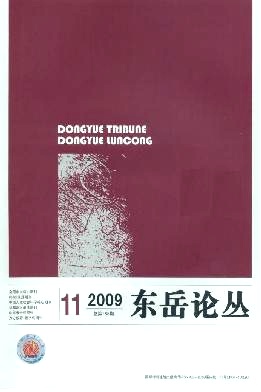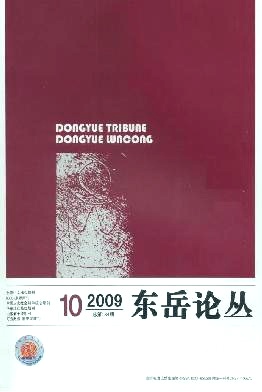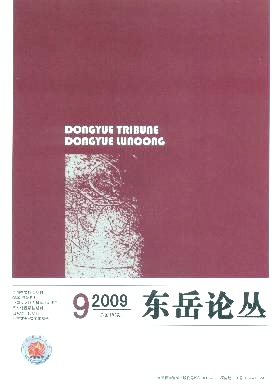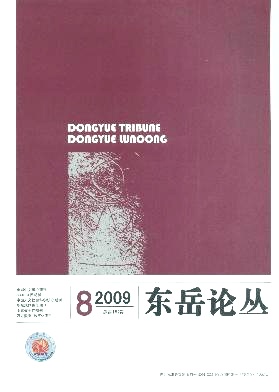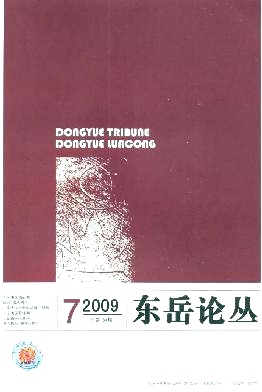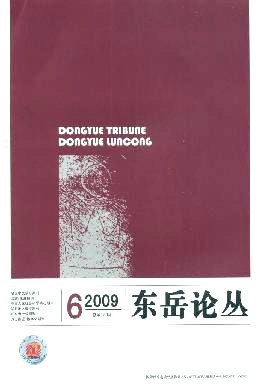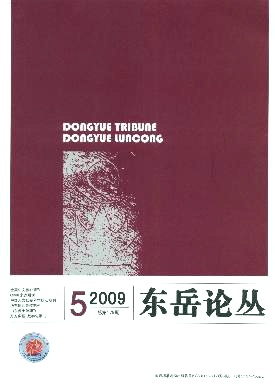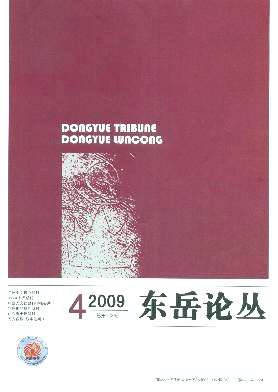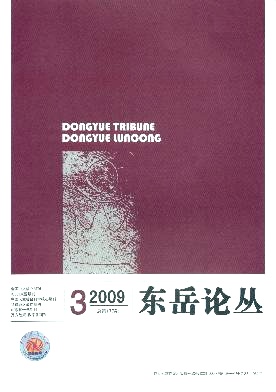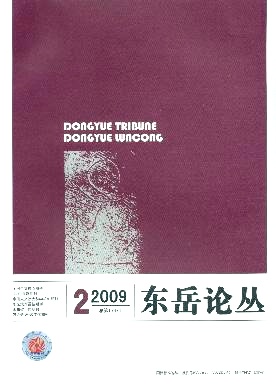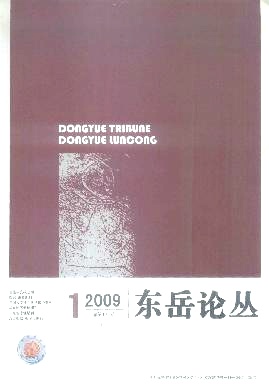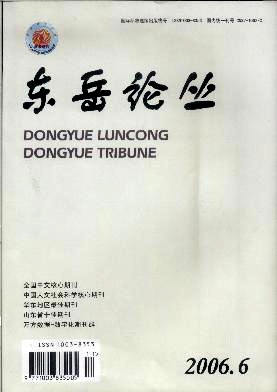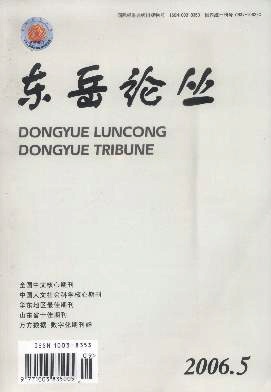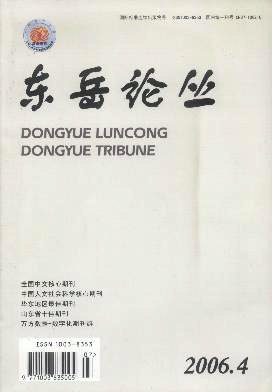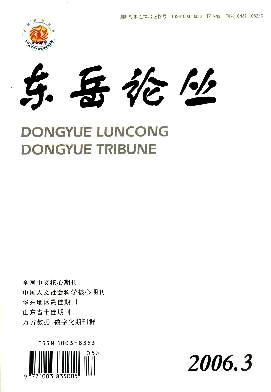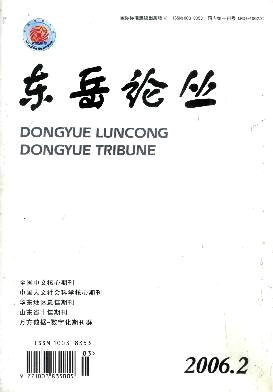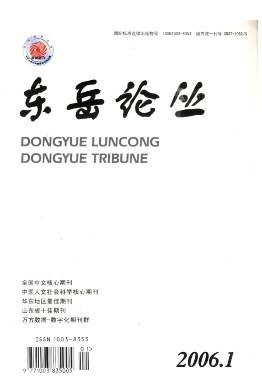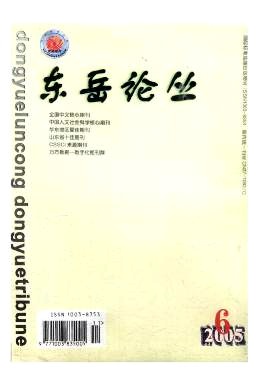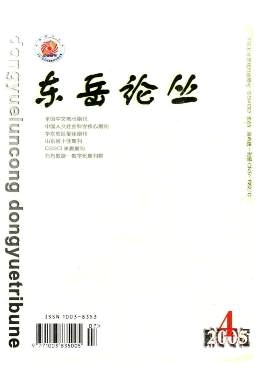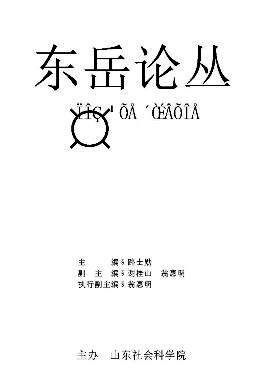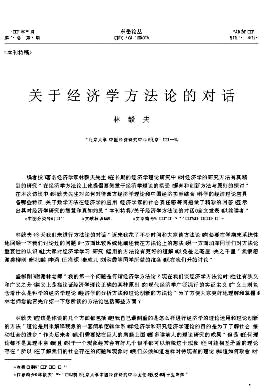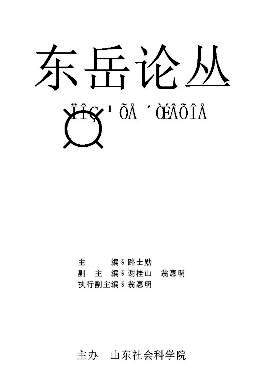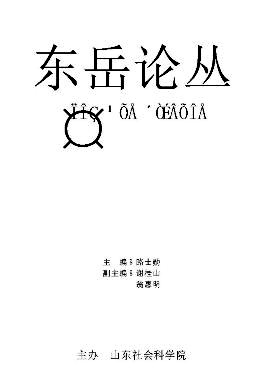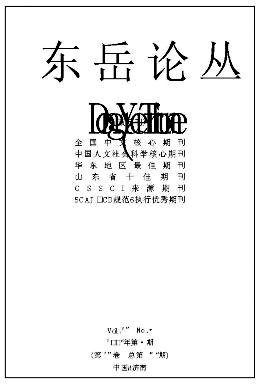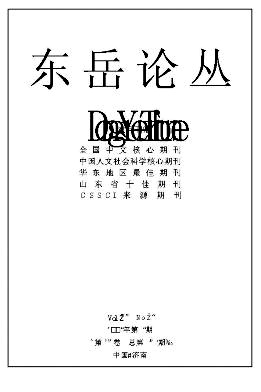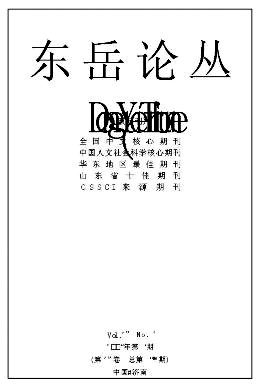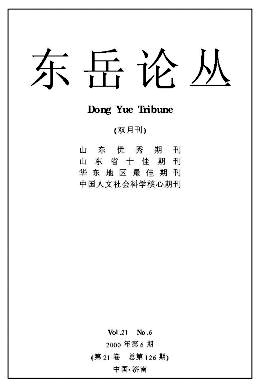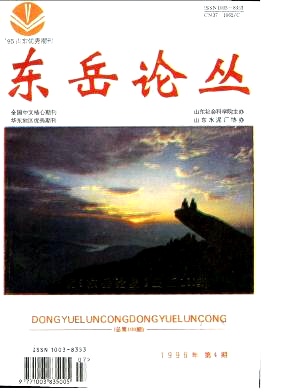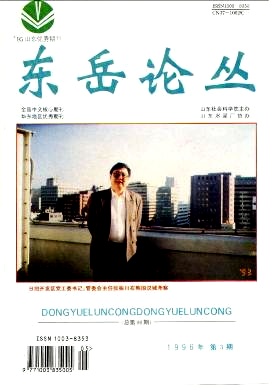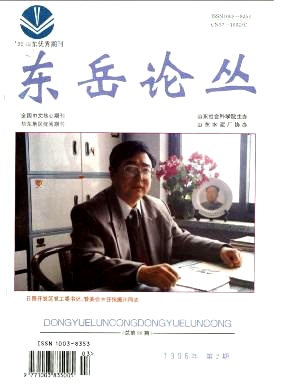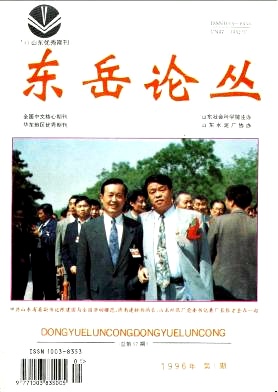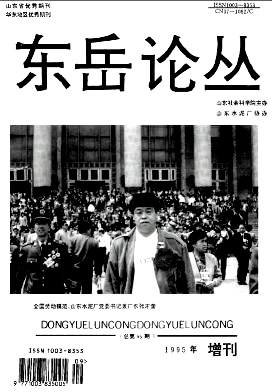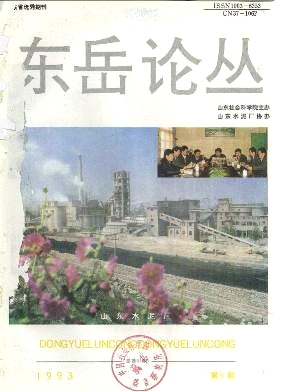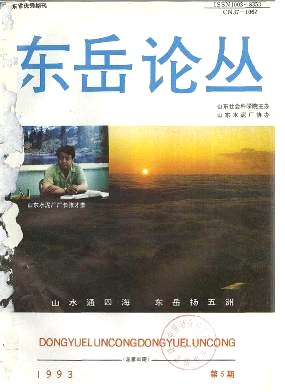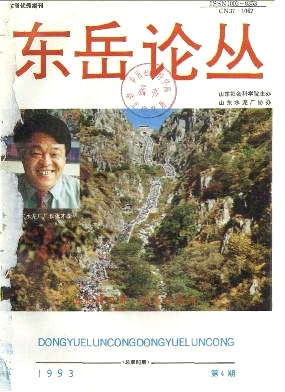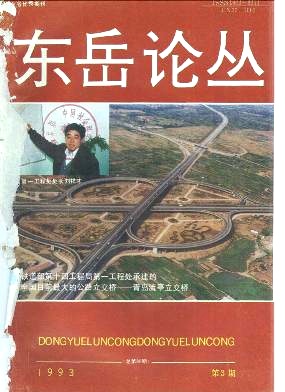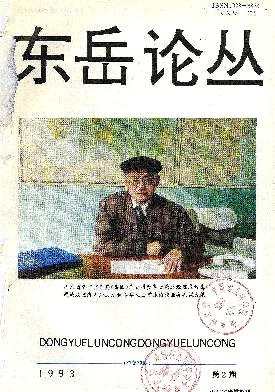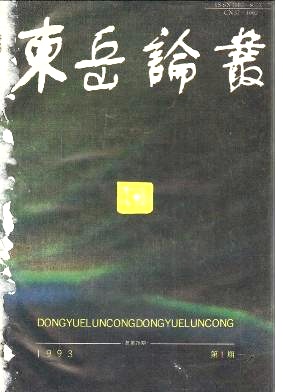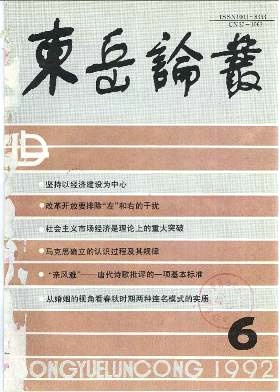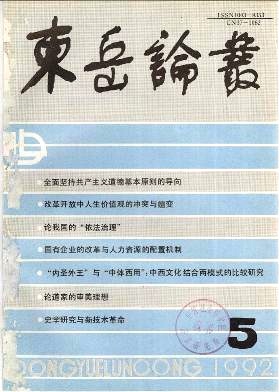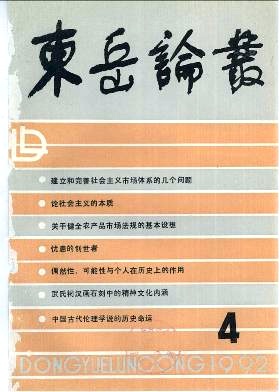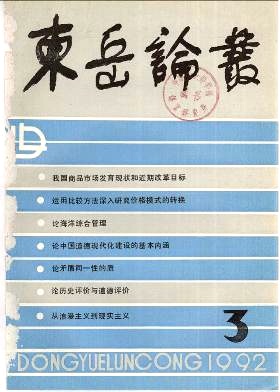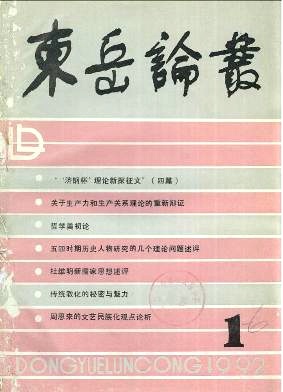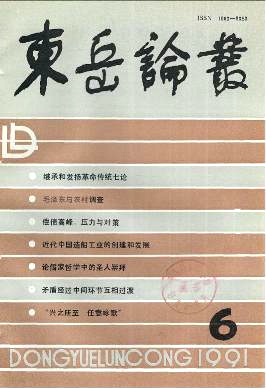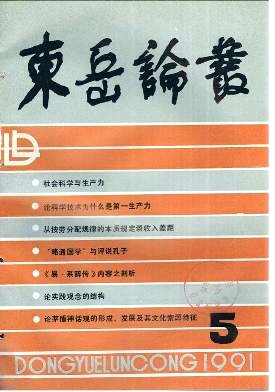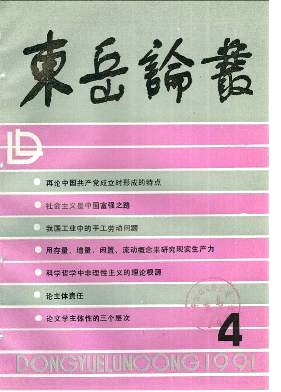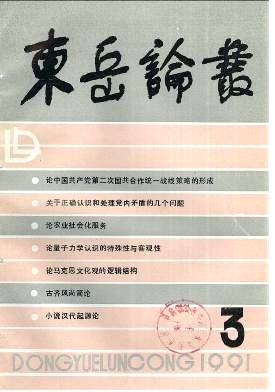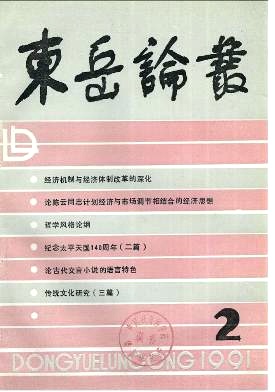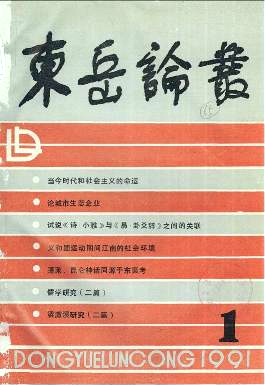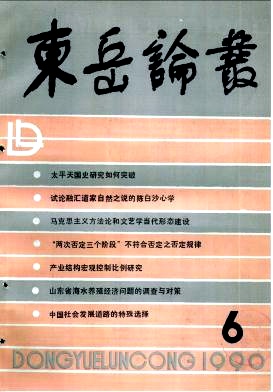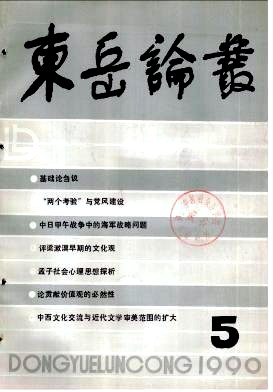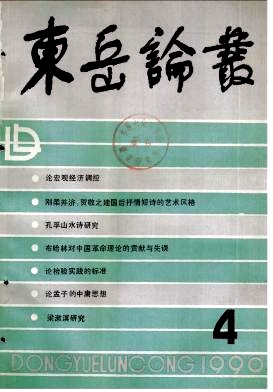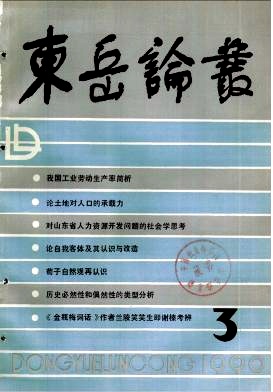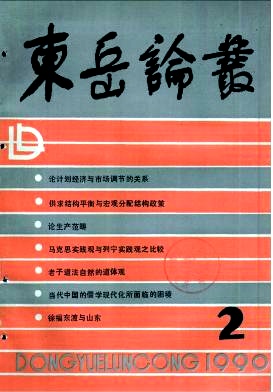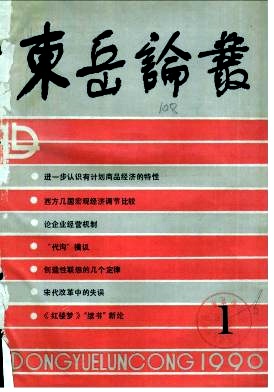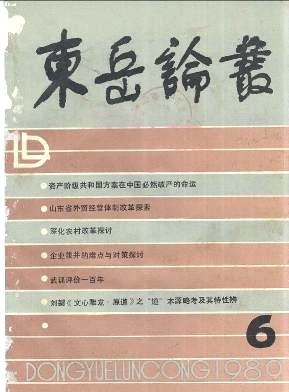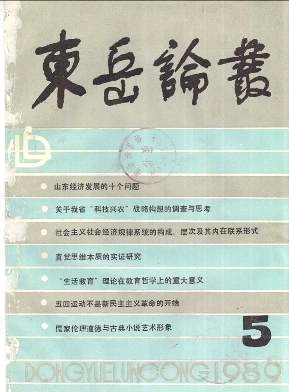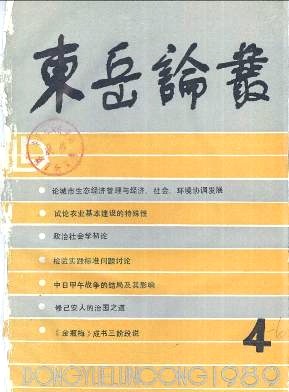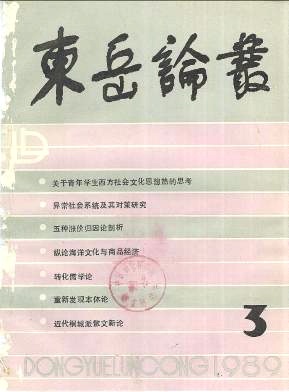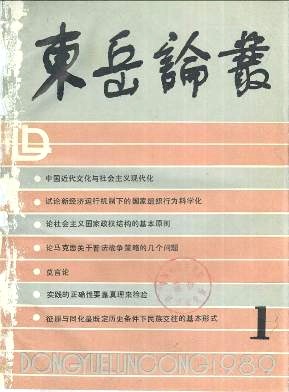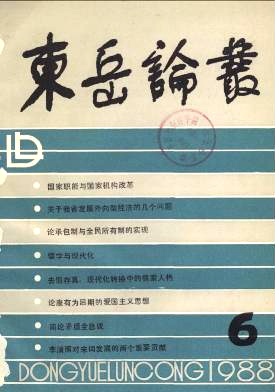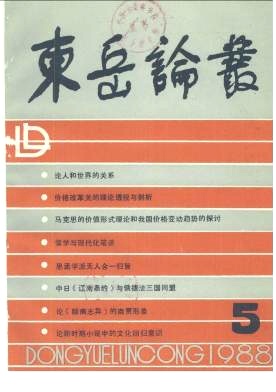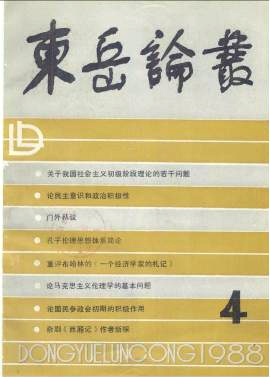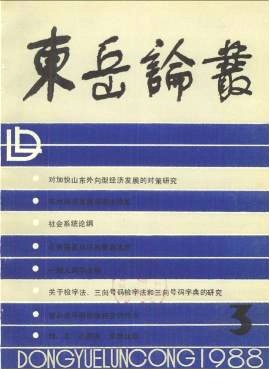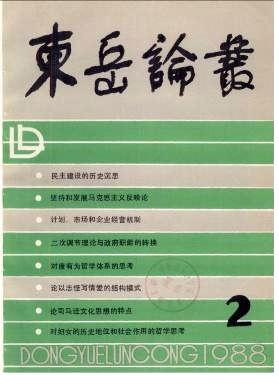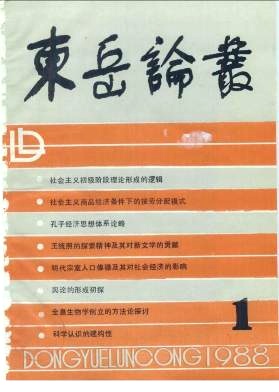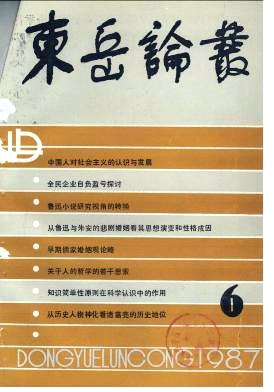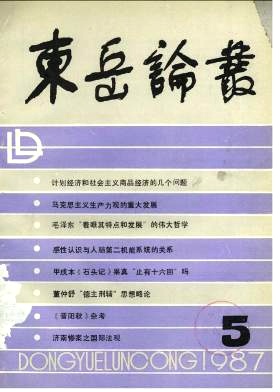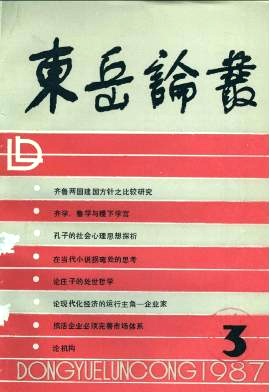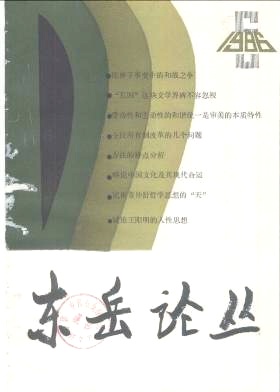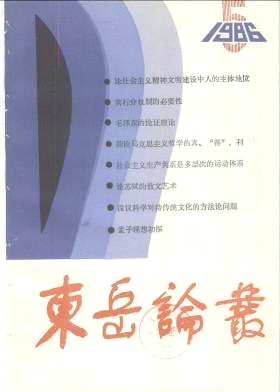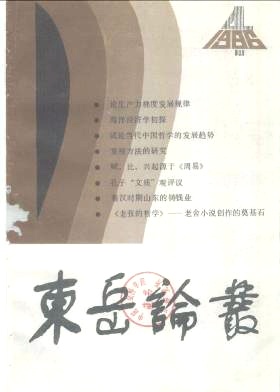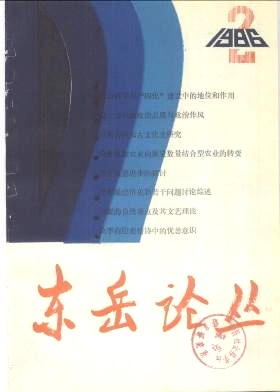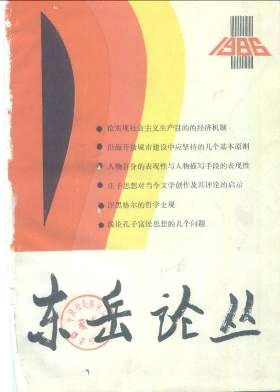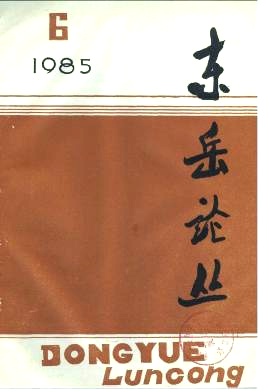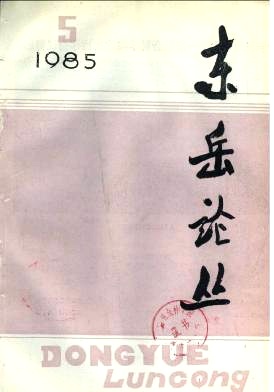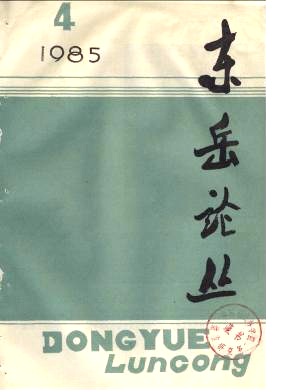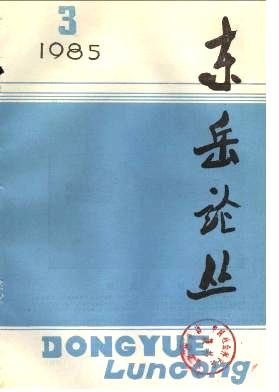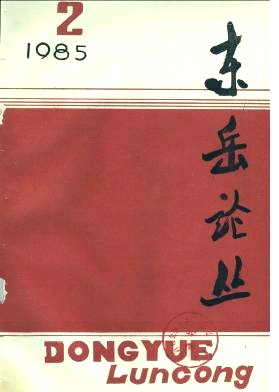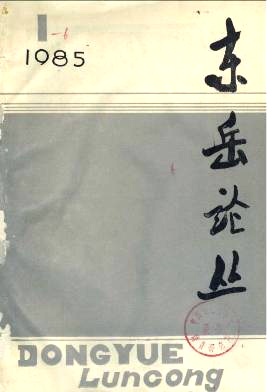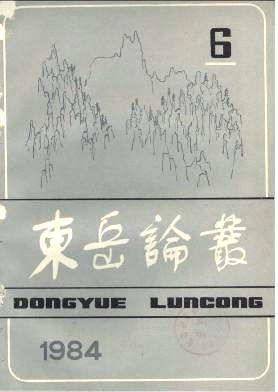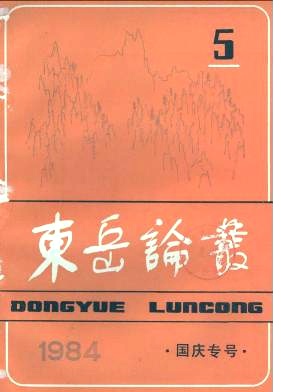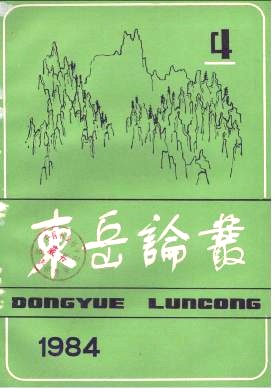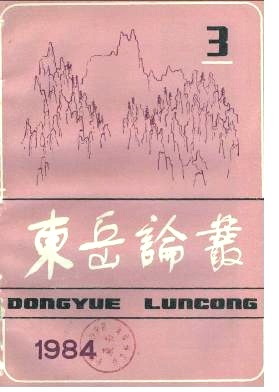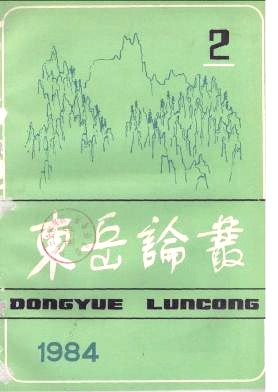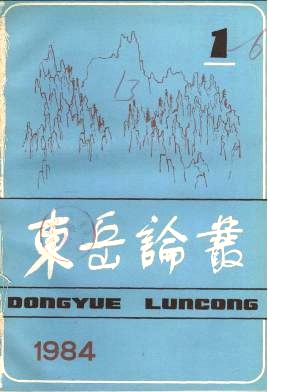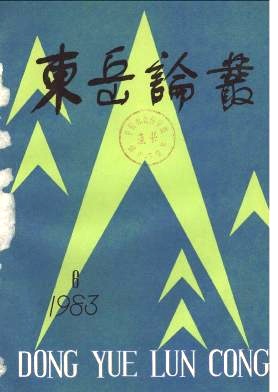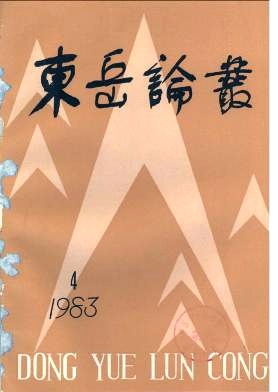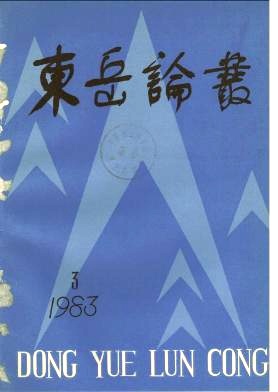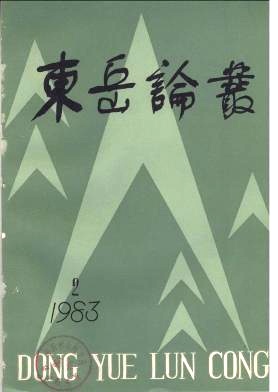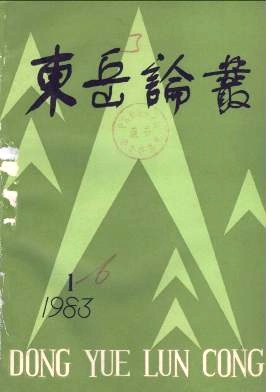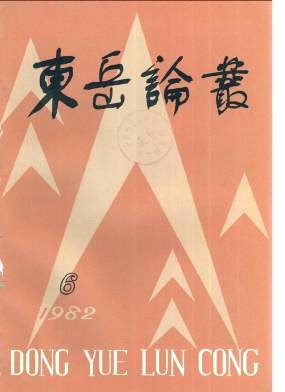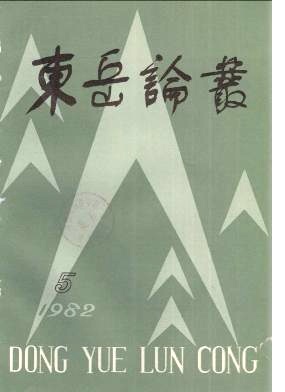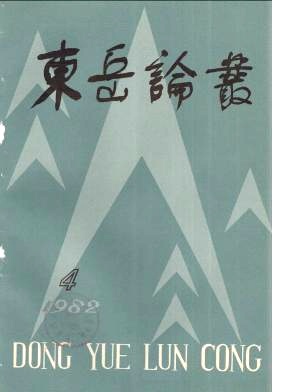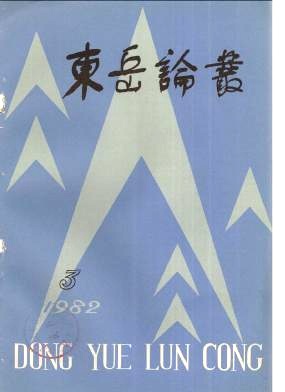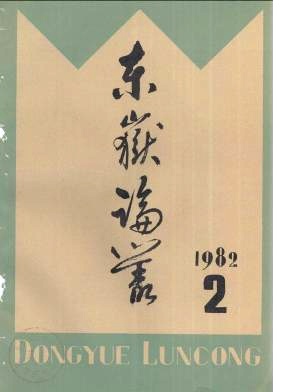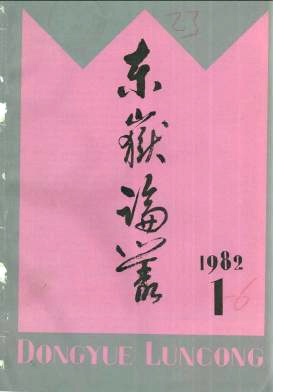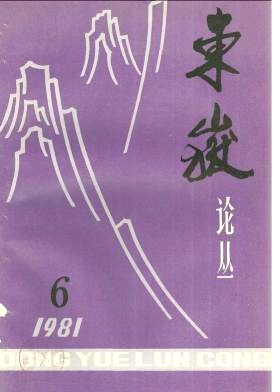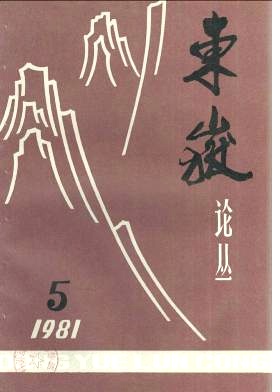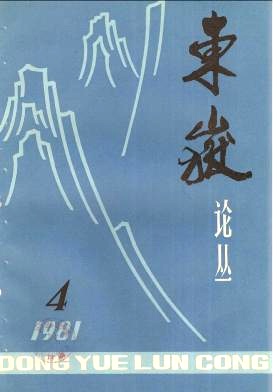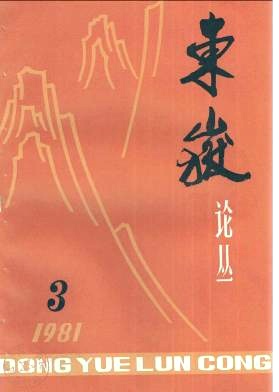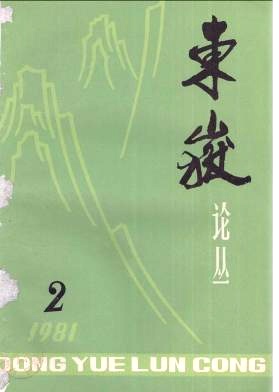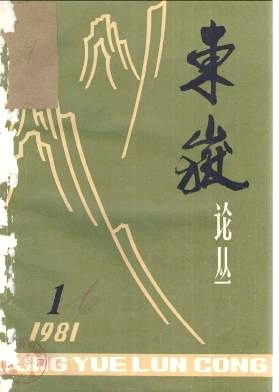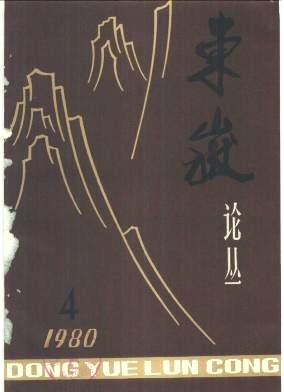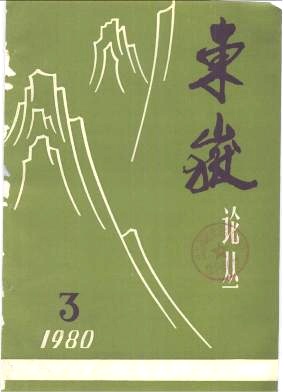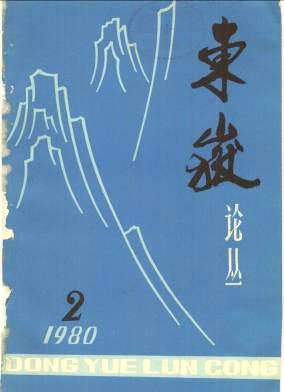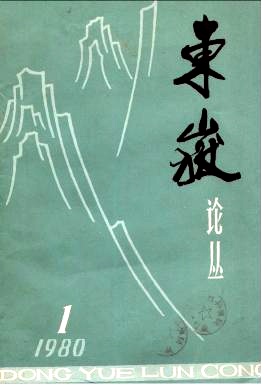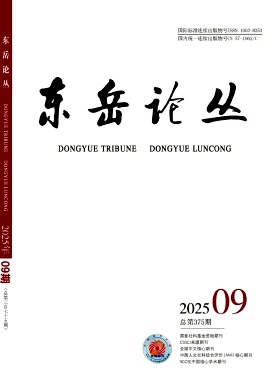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理“四风”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
张士海;张舒婷;“四风”是积习难改的顽疾,是党和人民的大敌。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包括在治理目的上坚持“纠”与“树”同时并举,在治理主体上坚持“党”与“群”有机统一,在治理对象上坚持“点”与“面”同抓共管,在治理内容上坚持“风”与“腐”同查同治,在治理方式上坚持“柔”与“刚”同向发力,坚决地同“四风”作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在“四风”治理的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必须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教育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以“关键少数”为抓手、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这对于在新征程上,更好地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持续筑牢人民对党的信任根基,进一步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代出场、结构体系与构建路径
赵付科;吴文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要求。建构中国发展新的话语范式、凝聚文明复兴的精神认同以及丰富人类文明样态中国元素的时代要求,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时代出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意蕴的独特性决定了其文化形态结构特质的系统多元性,文明性与民族性相契合的文化形态体系、历史性和现代性融通的文化内核体系、人文性与人民性互促的文化价值体系、切实性与前瞻性结合的文化叙事体系,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内容体系。新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要在自信自立中培铸文化品格,在体用贯通中开辟发展空间,在守正创新中续民族文脉,在文明引领中擘画文明前景。
刑天之舞与战士之死——鲁迅对陶渊明的接受与转化
侯桂新;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创作理念,“魏晋风度”对鲁迅的深刻影响都显而易见,但在这当中,来自陶渊明的影响历来被忽视了。事实上,陶渊明的诗文对鲁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并在他的文学世界留下了长长的投影。在青年鲁迅寻求精神界之战士的历程中,陶渊明《读山海经》对刑天之舞的歌咏为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本土战士形象,并催生出鲁迅笔下的战士形象。而在中老年鲁迅感悟生死、对自身的死亡进行凝视和书写时,陶渊明充满过客意识的《拟挽歌辞》和《自祭文》不但引发了他的创作动机和灵感,而且在作品构思和写作手法上为他所直接借鉴,鲁迅的散文诗《死后》和临终前辞别世界的散文《死》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和陶”之作。不过,鲁迅对陶渊明并非全盘接受,他舍弃陶渊明的平和静穆而推崇其“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并在创作中将陶渊明笔下的过客之死转化成战士之死,传达出他对不合理社会的批判态度与人生抗争精神。
鲁迅对方言文学的辩证审视——从其对《海上花列传》《何典》方言语体的态度谈起
孙文成;作为最早对《海上花列传》进行价值发掘的新文学家,鲁迅对《海上花》的认识与同对作品有揄扬、传播之功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刘半农有一个显著差异,即鲁迅对作品的方言语体态度有所保留。无独有偶,鲁迅对《何典》方言语体的认识并无不同。鲁迅对《海上花》《何典》方言语体的态度,是其辩证的方言文学观念使然。鲁迅深知方言文学奇警风趣、生动传神和具有地域风致的独特优长,但也洞悉理解困境这一方言文学的致命劣势。在发展大众语的特殊时代语境下,鲁迅提倡拉丁化的方言文学的发展。但实际上鲁迅提倡的是通过拉丁化的方言文学实现大众语文学的路径,即拉丁化的方言文学对于大众语文学的工具性质,而非拉丁化的方言文学本身,更非依旧保持汉字化的方言文学。鲁迅之所以对方言文学的理解困境十分关注,是因为他非常重视文学的传播效果。与鲁迅不同,胡适等人对于理解困境的态度泰然且乐观。而历史证明,相较之下,鲁迅对理解困境和方言文学的判断是更为准确的。
且介亭里读“村书”:《看图识字》与字学问题
陈澜;《且介亭杂文集》系列文本中鲁迅频繁提及汉字改革的问题,《看图识字》是其汉字改革思路中具有独特性的一篇。以《看图识字》为中心,勾连《选本》《门外文谈》《从“别字”说开去》《论新文字》等相关文本,展开鲁迅从蒙学出发批判经学的角度,揭示在《看图识字》这样的“村书”中包含的字学脉络,呈现字学问题上反映的中国传统内部具有革命性的一面。《看图识字》关乎集体日常的“读”与“写”,旨在强调字形与人的感官、感知的关联,作为理解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一个原始的、基本的角度,也集中反映鲁迅的汉字观,由此相关的系列文本指向鲁迅一贯的对于“文字障”的批判,构成了鲁迅的文字观、历史观中一个隐藏的思路,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学术性的面向。展开《看图识字》背后的“字学”脉络,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鲁迅汉字改革的思路、认识,科学地总结鲁迅思想的遗产,为理解“现代”语境下的中国文字与中国问题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